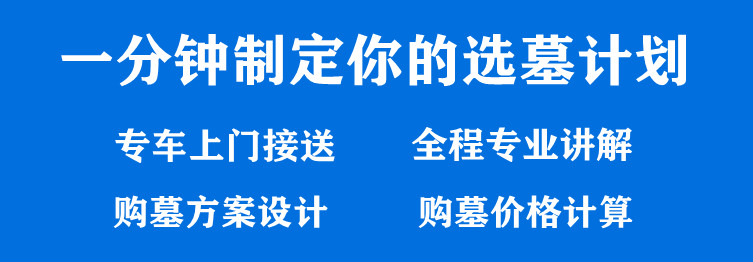《平娃的墓園》紅色故事 ——讀李秀兒的
一口氣讀完李秀兒的《平娃的墓園》,適逢我正在四川的大巴山中采訪,這里有許多紅軍和游擊隊的傳奇和故事,此類題材讀過一些,多數是正面直接描寫,印象不深,或者說還挖掘不夠。在我看來,小說畢竟不是為歷史正名或為歷史立傳——那是歷史學家和黨史研究者的事,小說只能描寫人物的命運。這類紅色故事如果只是新聞紀事或刻意宣傳,就落入了俗套。而李秀兒的《平娃的墓園》這部小說,卻從一個小紅軍不幸犧牲,一個農民家庭被動建起墓園下筆,開口很小,開掘很深,就此切入,將讀者帶進一個戰火硝煙的時代,并延續幾十年的風云變幻,寫出了大樹、小樹、新樹一家三代人的悲歡離合、起伏跌宕的人生。
我曾為李秀兒的第一本散文集《隨同行走》壽陽山墓園寫過序,在我印象中,她的散文不守成法,收放隨心,看似無意的閑筆經營,卻很打動人。沒想到她又用別致的小說筆調,向讀者呈現了一個不易寫好的紅色故事。
這篇小說寫得生動、有趣、好看,發人深思,其中不乏時代背景的斑斕色彩以及人物命運的無奈及潮起潮落的沉重,并從中透出些許樸素的人性光輝。故事其實很單純,就是寫一個紅軍墓地,三代守墓人。這樣的故事應該說更具有新聞宣傳價值,如何將這個故事寫成一篇動人的小說,委實不易。而李秀兒下筆從容,扣住主人公三代的命運落墨,將一波三折的故事放在時代風云變幻的脈絡展開,令人唏噓不已,掩卷長嘆或有感同身受的難言意會。
故事開頭,一個小紅軍受傷,紅軍團長委托當地老鄉照看,結果小紅軍傷重去世了。當時戰亂年代,各種勢力呈拉鋸戰,不同的軍隊在這個小山村進進出出。作者很生動地將各種軍隊用詼諧的筆調概括為灰衣軍、藍衣軍、黃衣軍、黑衣軍、綠衣軍、雜衣軍。分別是紅軍、滇軍、國民黨中央軍、黔軍、川軍、雜牌軍。面對小紅軍的后事,不同的軍隊表現不一。比如藍衣滇軍到了,說“還不快埋了,你是等著中央軍來找麻煩嗎?”黃衣中央軍到了,因為抓紅軍有賞,便要敲詐勒索。不料這黃衣軍對大樹的媳婦施暴,一時之間,大樹怒傷了這個黃衣軍,就此逃跑,去馬幫當了腳夫……
幾歲的小樹跟父親大樹在馬幫成長。
后來小樹的兒子新樹學了考古專業。
時光流水般過去。
小紅軍靜靜地躺在墓園,卻又經歷了不平靜的風風雨雨。小說將幾十年的風雨化成了墓地的風云。解放了,土改了,分地了,要劃成分了,大馬鍋頭的成分劃分成了難題;公社成立了,因為守護紅軍墓,民政部門要開錢,而要證明紅軍墓又成了難題,紅軍團長留下的證物——一紙寫有五枚銀元的證明和六顆子彈怎么也找不到了!終于等到已是司令的紅軍老團長二進山村了,紅軍墓才得到證實。
故事還沒有完。作者針腳嚴密地收尾。
后來,改革開放了,社會發展了,要修鐵路了,高鐵線路要穿過這片墓園。固執的守墓人當初在房地產商人引誘面前不愿意拆遷。小紅軍出現了,當然是在夢中,他想坐高鐵回到他的家鄉——江西。于是,守墓人——八十歲的老人小樹終于出乎意料地同意了。墓地遷到虎頭山了,小紅軍終于如愿以償,能從另一個世界坐車回到他的故鄉了。而在拆遷中,在老墻的斷垣殘壁中竟然發現了當年老團長留下的信物:證明、銀元和子彈!故事完滿的結局。這似乎符合國人的審美需求。不過,這傳統意義上的小說結尾也似乎無可非議,因為所有的小說結局都不外這三種結局:大團圓,一把火或一場災難一切歸零,或者開放式結局,主人公走了,不知所終。
作者將八十年的風云際遇濃縮地織進了這部不長的小說中。行文干凈,簡略得當,多有典型概括和寓意,許多細節作者也照顧得周詳。這類題材的小說,多半是直接寫當時的故事,或者是后來某人回憶當初,很少能將幾十年前的事植入往后幾十年中的現實中去。這篇小說在構思上卻巧妙地將兩者結合起來,全靠這個幾十年不變的墓園為全篇布局。另有一些人物的描寫,比如大樹的媳婦菊花,馬鍋頭張長水,后來小樹的愛人杏兒等,都各有故事和情節,穿插其間,各司其職,讓作品豐滿有致。作者沒有泛濫的鋪排、抒情和議論,文字簡約優美,格調輕快中略帶憂傷,深得小說的三味。
小說里呈現的有克制的東方喜劇色彩,也為小說加分不少。這種喜劇,是亦莊亦諧、莊諧得體的喜劇,是將批判鋒芒內化收斂之后的喜劇,是擦去悲傷淚痕留下矜持大度微笑的喜劇,是使敘事鋪排要言不繁的喜劇,也可以說,是一種很有品味的真正的喜劇。比起那些反智商的“神劇”,那些低智商的“紅色”故事來,這部小說自有其含蓄優美的輕喜劇風格。
我曾經在作者散文集的序中說,李秀兒的寫作可能會是她人生的另一路選擇和發展,她的細微觀察,對事物的敏感,對人物和人生的上心,加上她能準確并從容敘述的文字,沒準會將習慣的言說(她原來做過電視主持人)化為更多的文字。但愿她在小說的創作上更上層樓!

掃碼添加客服【免費獲取購墓方案】
全程指導,專業講解,專車接送